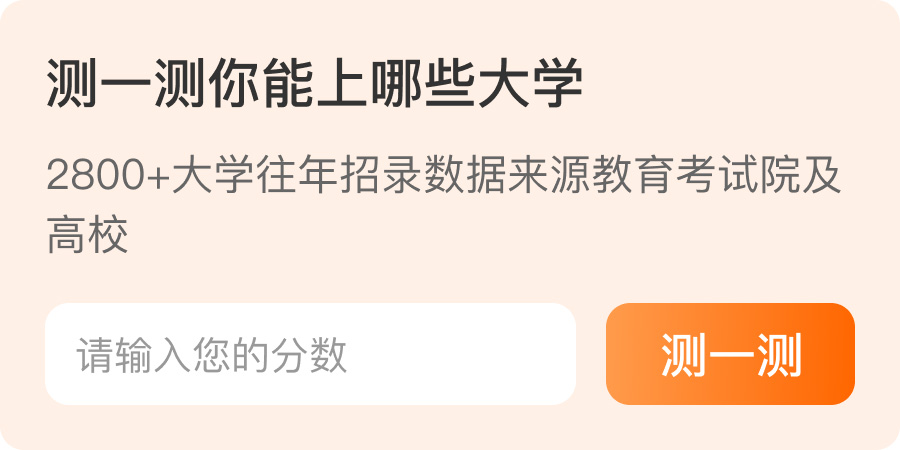《中國科學基金》 | 陳國強、張俊:聚焦臨床關鍵科學問題 充實科學基金資助體係

張 俊1 陳國強2,3*
1.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 腫瘤科
2. 海南醫學院 海南省醫學科學研究院
3.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 腫瘤係統醫學全國重點實驗室

陳國強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學部委員,海南醫學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腫瘤係統醫學全國重點實驗室主任。主要從事腫瘤和白血病細胞命運決定及腫瘤微環境調控機製研究,在白血病細胞分化和死亡調控機製及其幹預,白血病幹/祖細胞幹性維持和腫瘤微環境形成機製以及抗白血病藥物靶標和先導化合物發現等方麵取得了係統性創新成果。多次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國家教學成果獎一等獎、中華醫學科技獎一等獎、上海市自然科學獎一等獎、上海市科技進步獎一等獎、上海市教學成果獎特等獎以及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等獎項。

張俊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腫瘤科主任,上海臨床研究中心倫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抗癌協會腫瘤支持專委會候任主委、中國臨床腫瘤學會血管靶向專委會副主委。主要從事抗腫瘤新藥臨床研究和化療壓力驅動下實體腫瘤的進化機製研究。曾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教育部自然科學獎二等獎、上海市科技進步獎一等獎等獎項。
摘要
臨床科學研究是我國醫學界實現“原始創新”與提供“中國證據”“中國數據”“中國方案”的關鍵抓手。近30年來,我國在臨床研究監管體係、基地與平台、隊伍建設以及成果產出等方麵取得長足進步。但我國臨床研究的源頭創新和臨床轉化能力相對薄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以下簡稱“科學基金”)作為推動基礎研究源頭創新的核心力量,在我國醫學科學發展中始終發揮關鍵引領作用。麵向我國臨床研究領域亟待解決的重大需求、關鍵臨床科學問題和技術瓶頸,如何引領醫學科學領域的研究方向,並以此契合臨床重大需求及應用轉化、激發臨床研究者的創新源動力、鼓勵基於臨床關鍵科學問題的自由探索臨床研究,是科學基金需要直麵和解決的時代命題。本文就我國臨床科學研究的現狀、科學基金資助臨床研究的模式與效能、科學基金支持臨床研究實施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問題與解決方案等做了初步調研並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臨床科學研究;科學基金;戰略布局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指出,健康是促進人全麵發展的必然要求,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條件[1]。臨床科學研究是橋接基礎醫學研究的關鍵環節,也是我國醫學界實現“原始創新”與提供“中國證據”“中國數據”“中國方案”的關鍵抓手[2]。隨著臨床研究在現代醫學體係中的權重不斷增加,我國臨床醫學在心腦血管疾病、腫瘤等重大慢性複雜疾病和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及基於醫學大數據賦能的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等方麵麵臨著更為嚴峻的挑戰。
為更好發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以下簡稱“科學基金”)在醫學科學領域的引領效應,激發臨床創新策源能力,提升科學基金資助效能,將臨床科學研究成果最終轉化為人民的健康,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以下簡稱“自然科學基金委”)有必要進一步加大科學基金對臨床研究領域的資助部署力度,並優化資助模式。本文從臨床研究組織者的角度,通過文獻檢索、現狀調研等方式,梳理了目前我國臨床科學研究的現狀、盤點國外科學基金支持臨床研究的模式和資助效能,並提出可能存在的問題和解決建議。
1.我國臨床科學研究的現狀
麵向新時期國家健康戰略的重大需求,我國醫藥衛生領域科技發展目標正逐步實現從“以治病為中心”向“以健康促進為中心”過渡,從闡明疾病機製、預防幹預、藥械研發、智慧醫療等全方位提升我國醫藥科技水平[3]。在國家經費投入和管理方麵,逐步形成了自然科學基金委、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等不同管理機構,從基地、團隊、人才、項目、轉化等角度,協同資助和管理臨床科學研究。我國醫學受眾群體龐大、病種多樣、醫療資源豐富,但開展高質量臨床研究卻麵臨著不少瓶頸,具體表現為:大多數臨床醫生學科背景單一、臨床工作繁重、資深或戰略型臨床科學家較少、具備豐富臨床研究經驗的研究者隊伍建設有待加強、臨床研究方法學相關理論和規範的原始創新驅動力不足、臨床研究數據共享機製有待完善等[4]。
通過檢索美國國際臨床試驗注冊中心、歐洲臨床試驗注冊中心、英國國際標準隨機對照試驗注冊庫(International Standar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Number,ISRCTN)、日本大學醫院醫療信息網、澳大利亞—新西蘭臨床試驗注冊中心、伊朗臨床試驗注冊中心、印度臨床試驗注冊中心及中國臨床實驗注冊中心等8個臨床研究注冊平台數據,結果顯示:在2020—2022年間,中國研究者的臨床注冊數分別為16 383項、17 527項和16 183項,3年注冊總量占全球注冊總量的23.91%(圖1);且中國學者在臨床研究領域的論文發表數量占全球總數17.3%(圖2),但在Lancet、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JAMA)、British Medical Journal (BMJ)、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NEJM)等主要同行評議期刊上發表的臨床試驗論文數較少,以2022年統計結果,分別為17篇、16篇、12篇和19篇,僅占發表總量的5.99%。我國開展的臨床研究雖在全球範圍內占比較大,但表現為注冊數量多、發表成果少,領銜國際多中心的研究則更少。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網站上中國藥物臨床試驗登記數量達11 520項,但在藥物臨床試驗登記與信息公示平台上,國際多中心研究僅占8%。

圖1 2020—2022年全國臨床試驗注冊數量分析

圖2 2016—2022年全球及中國臨床試驗發文數
2.科學基金資助臨床研究的模式與效能
2.1 科學基金支持臨床研究的布局與模式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U. S., NIH)通過兩大布局資助臨床科學研究[5],一是位於總部的臨床中心,以醫院—實驗室的模式,集中開展臨床實踐與臨床實驗,兩者並重;二是通過支持臨床與轉化科學獎勵計劃,在全國範圍內設立研究中心,鼓勵臨床創新研究。該機構2021—2025年報顯示[6],用於支持臨床研究的直接經費每年超過30億美元,並在資助格局上呈現為健康促進、疾病預防、新療法/治療的三位一體格局。2008—2018年間,NIH臨床研究資助占比為10%~14%,2019年NIH絕對資助經費達58.91億美元。基於該布局,美國臨床研究的項目負責人(Principle Investigator,PI)數量急劇增加,相對而言,從事基礎研究的PI比例從42%下降至14%。
為更加明確地區分NIH所資助的臨床研究和以藥品和器械上市為目標的企業發起研究(Industry Sponsored Trial, IST)之間的不同,NIH於2014年修訂並發布了其資助範圍內臨床試驗的定義[7],關鍵要素包括:支持臨床高度優先級問題的判定;避免不必要地重複先前已開展過的試驗;對公共資源進行適當管理,部分方法是開發和維護支持臨床研究的可靠數據;尊重臨床研究參與者的道德義務;促進廣泛、透明、及時和負責任地發布臨床試驗信息等,最終體現“從發現到治療、從治療到治愈、從治病到健康”的目標[8]。
自然科學基金委醫學科學部自成立15年來,始終秉承醫學初心,以健康為目標,有步驟、有邏輯地引導中國醫學科學研究的戰略布局,堅持以科學問題為引導,以臨床轉化為目標,穩步釋放臨床醫生的科研創造力;開展有價值和市場導向的卓越研究。具體舉措包括:改革申請代碼(以腫瘤學科代碼改革為例,將原先以“瘤種”劃分申請代碼改革為根據“關鍵科學問題”設定申請代碼);設立“基於臨床關鍵科學問題的臨床研究”專項(每年資助50項),臨床—基礎結合的雙負責人製度(Co-Principle Investigator, Co-PI)等。盡管如此,目前在中國臨床實驗注冊中心注冊的研究中,標注科學基金支持者僅占9%。科學基金作為推動我國基礎研究發展的主力,應更有力承擔起基礎向臨床轉化的支撐作用,加快建立對臨床研究的支持計劃,突出科研引領特色,推動國內臨床研究的發展[9]。
2.2 科學基金支持的臨床研究的方向與定義
與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中醫藥管理局等行業管理部門及企業支持的臨床研究不同,科學基金作為推動基礎研究源頭創新的核心力量,其所支持的臨床研究更應強調源於臨床實踐且具有重要臨床意義:在問題凝練上,建議以科學原理認識、科學機製發現、新型技術革新為基礎和出發點,樹立麵向解決人口健康問題的臨床需求導向;聚焦疾病診斷、治療和預後的關鍵科學問題或技術難題,以麵向人民生命健康、改善健康結局及優化臨床實踐為目標;開展高質量的臨床前研究、臨床研究、乃至罕見病個案研究等。科學基金所支持的臨床研究範疇應體現前沿與創新,涉及機製,具有探索性、發展性、先導性、可行性、實用性、行為性和其他幹預性等特性,也應包括真實世界的研究等。另外,臨床研究與IST並行將更好地推進藥物研究的發展,從而為循證醫學提供更多證據[10]。
2.3 科學基金支持臨床研究的管理模式
以美國NIH為例,其堅持引導基礎學科向生物醫學領域彙聚,突出“化發現為健康”的戰略目標,通過“轉化醫學中心”和“臨床研究中心”兩大中心部署臨床研究。在資助形式上,既有“癌症登月計劃”“精準醫學計劃”等優先級別的任務集成,也有涉及幾乎所有健康領域的全麵覆蓋。既有針對特定疾病的研究項目,也有臨床研究方法學的探索。上述工作推動了國家範圍內的生物醫學研究與藥物研發進展,打造了臨床與轉化研究協作平台,成功在埃博拉病毒感染、腫瘤、神經係統疾病、衰老等重大疾病和健康問題方麵,引領前沿基礎研究走向臨床實踐。
在我國,2010—2022年自然科學基金委醫學科學部共資助研究10餘萬項[11]。以2021年計,麵上項目、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地區科學基金項目共資助10 547項,其中臨床科學研究的項目主要集中在人群隊列研究以及臨床診療新技術的應用研究等方向。2021年,醫學科學部設立“基於臨床診療關鍵科學問題的基礎研究”專項基金,進一步充實了科學基金的資助體係,體現了科學基金在引導和管理以“源頭創新為驅動、解決臨床科學問題、積累高水平循證醫學證據”為目標的臨床研究資助模式、發展規劃以及保障措施方麵做出的創舉。該專項基金的設立體現了科學基金的特征,相關的研究類型包括:由研究者發起的基於臨床診治實踐的原創性重要科學問題研究、基於前期基礎研究成果轉化於臨床實踐的探索性研究、與解決臨床診療關鍵科學問題相關的新型研究方法與範式的探索。在項目設立方麵,強調基於臨床痛點與難點科學問題開展基礎研究的定位,推進研究體係建設、範式革新和項目管理格局的革新(全生命周期管理與數據共享等),加強評議流程與專職管理隊伍建設,加強以臨床科學研究主要發起者和執行者為主的臨床科學家隊伍建設等。
盡管既往對臨床研究的資助強度處於較低水平,但科學基金擁有豐富的項目監管經驗、規範的評審製度、公正科學的管理製度以及資深的臨床醫學專家隊伍。依托於上述優勢,自然科學基金委通過加強頂層設計,整合優勢資源,發揮資助導向作用,完善科研評價體係,規範數據和成果共享等,定能更有效地提高我國臨床科學研究水平[12]。
2.4 科學基金支持臨床研究的效能
NIH支持臨床研究的資助效能,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麵:促進健康、革新科學和服務社會。代表性成績包括破譯控製生命過程的遺傳密碼、展示化學物質如何在神經細胞間傳遞電信號、描述蛋白質化學組成及其折疊生物活性構象之間的關係等。這些基礎研究的發現加深了人類對遺傳性疾病的理解,也將會催生更好藥物研發等。近年來,高強度的長期連續資助和戰略引導成功地催生了冠狀動脈搭橋手術、分子靶向藥物治療腫瘤等諸多具有裏程碑式意義的醫學科研成果,有效地逆轉了原有疾病的不良結局,並產生了顯著、廣覆蓋且持久的臨床成效。另外,美國心髒病死亡率從1977年到1999年下降了36%[13]、同期腦卒中死亡率減少50%、惡性腫瘤死亡率自1991年起持續下降(累計減少了300萬腫瘤死亡人口[14])、美國癌症死亡率從1991年至2022年下降了32%(癌症生存者總數達到1 800萬)等極具臨床成效的事件,表明“Bringing Science to Life”的目標正在逐步實現。
3.科學基金支持臨床研究實施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問題與建議
3.1 進一步提升前瞻性戰略布局
美國等國家持續加強生物醫藥領域的投入,用於探索疾病本質和改善臨床結局,並在重大傳染性疾病、重大慢病、新藥創製、重大裝備研發等領域不斷布局。NIH近10餘年來的代表性布局包括[15]:精準醫學(2011)、推進創新神經技術腦研究計劃(腦計劃,2013)、癌症登月計劃(2016)等。近年來又提出新思路:每5年製訂一項整體層麵的宏觀戰略規劃——“NIH-Wide Strategic Plan”(NIH拓展戰略規劃)以確定優先研究領域,以期滿足日新月異的醫學發展願景和目標。
圍繞科學基金的四個使命任務:推動學科均衡協調可持續化發展、推動基礎研究進步、人才培養、促進自然科學研究的國際合作與交流,我們建議在醫學科學領域進一步鼓勵和引導醫學科學研究重心回歸臨床初心,引導臨床醫生將時間還給病人,並以“能解決病人痛苦的重要科學發現、科學發明”為目標打造具有中國原創力的臨床科學家隊伍,凸顯醫學科學的臨床特征,體現科學基金的科學研究特色,讓國家的科研投入轉化為“人民健康指標的改善”和“中國臨床科學家隊伍在醫學發展中競爭力的提升”[16]。
麵向我國人民健康維護和重大疾病防治中的關鍵臨床問題,科學基金應堅持“臨床實踐發現,科學研究發明,成果證據發表,健康結局改善”的原則,引領中國醫學科學領域方向,鼓勵基於臨床關鍵科學問題的創新研究。努力積累中國數據、夯實中國證據,推動中國指南,打造中國醫學科學研究團隊,並對標科學發展的要求、醫學科學進步的要求、國家投入基金的要求、市場導向和健康目標的要求、以及提高科學基金管理效能的要求。
3.2 優化科學評價體係,激發臨床創新策源能力
臨床醫學的創新策源驅動力包括提出臨床關鍵科學問題及解決方案的能力。前者源自臨床醫生的實踐和靈感,後者包括平台、裝備、人才、基金資助政策、科研評價和管理製度等保障;臨床醫學的創新策源驅動力是以達成全麵提高卓越人才自主培養、加快實現高水平醫學科技自立自強為目標[17]。臨床實踐是驅動和產生關鍵科學問題、解決患者病痛之重要科學發現的源泉[18],科學基金的引領效應,還應體現在將臨床醫生,尤其是具備原創性科研能力和科研實力的臨床科學家的創造力激發出來,避免一味追求小而全的套路化、模式化的“機製研究”,進一步彰顯醫學科學研究的臨床屬性,探究疾病本質,改善臨床結局。
在原創性藥物研發和學術引領方麵,NIH通過設立職業生涯支持的各類人才項目、小微企業創新性科研項目等,支持創新性人才培養和新藥、新械研發。如NIH資助的Brian Druker博士針對BCR-ABL激酶信號傳導研發藥物伊馬替尼用於治療部分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和胃腸間質瘤,開創了分子靶向治療的新時代。基於腦科學專項,新藥KarXT使8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消除了妄想和幻覺等。
我國目前用於學術評價和績效考核的通用手段,多以論文數量和影響因子等量化指標進行管理,並循此決定聘任、薪資、升遷、學術資源分配等。此類因過於強調SCI論文與影響因子而弱化其他指標的做法,帶來的後果就是科研人員熱衷於追隨國際研究熱點,寧願做重複性、移植性的工作,也不願嚐試有一定風險但可能有巨大影響的原創性研究工作。據《科學引文索引》分析,2020年中國作者共計發表55.26萬篇論文,連續第12年位居世界第2,僅次於美國。但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12.87次,雖較2020年統計時提高了7.8%,但仍低於世界平均值13.66次/篇。上述情況體現了我國學者專注於論文的“數量”,卻忽略論文的“學術影響力”。經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圖書信息中心檢索,2010—2019年全球發表的臨床試驗論文合計315 210篇,其中中國研究人員發表23 113篇(占比為7.33%);2010—2019年Lancet、JAMA、BMJ、NEJM 四大醫學期刊主刊發表臨床試驗論文共計3 689篇,其中中國研究人員發表47篇(占比為1.27%)。其中後者還有不少是企業發起的新藥、新械研究成果,而少有基於源頭創新的高質量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因此,我們建議在臨床研究項目和臨床研究人才評價體係中,應偏重臨床價值和臨床轉化的評估,構建客觀公正的科學評價體係,在體係中引入“創新效率值”等評價新要素[19]。
3.3 完善科學基金資助臨床研究的全生命周期閉環管理
(1) 組織結構:建議醫學科學部設立臨床研究處,進一步加大對臨床研究領域的支持力度、項目及人才的管理力度;並吸納更多的臨床醫學專家進入同行評議專家隊伍。
(2) 激勵原則:鼓勵臨床及轉化研究方法學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臨床及轉化研究方法學的理論創新是推動該領域發展的關鍵。研究方法的優化和創新可以提高研究設計、數據分析和結果解釋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在臨床及轉化研究方法學中,實踐探索是關注實際操作過程中的問題和挑戰,並嚐試用新的方法和技術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20]。通過實踐探索,可以發現和改進方法學中的缺陷,提高研究的可行性和可靠性,開展前瞻性研究。臨床及轉化研究方法學的創新依賴於跨學科的合作及多學科專業人才的協同培養。同時,臨床及轉化研究方法學可以借鑒其他學科的經驗和方法。例如,數據科學、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領域的創新方法可以為臨床及轉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解決方案[21]。
(3) 臨床研究專項申請書更新:包括醫學倫理審查和知情同意過程的細化規則,人類遺傳信息資源管理的要求等。在申請書前部增加要素清單是一個較好的方式來體現臨床研究的特色和要求,可使評審同行在閱讀申請書時更清晰地了解臨床研究項目的特色和相關要求。它還可以幫助申請人確保申請書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並確保各個環節都被充分考慮和體現。同時,參考國內外相關的臨床研究指南和標準,逐步優化和完善這個清單,以適應不斷變化的臨床研究領域的要求。在不更改目前申請書格式和布局的前提下,更好體現臨床研究的特色。其他相關要求可參照國家藥品審評中心、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等有關醫學科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執行。
(4) 臨床科學家隊伍建設:推動臨床研究團隊和臨床科學家隊伍建設。在麵向傑出的臨床科學家培養方麵,設立“青年臨床科學家”專項人才基金,甚至從職業生涯角度做到全周期支持。加強臨床科學家資助力度,鼓勵願意做科學研究的優秀醫生開展基於臨床關鍵科學問題的研究,鼓勵臨床醫生與基礎研究科學家開展合作研究。
(5) 分類評審和專項管理體係:實施臨床專項的分類評審,以凸顯臨床研究專項的特色。在項目管理流程方麵,更偏重臨床價值和臨床轉化的評估,以“年檢製”促進入組效率,“退出製”提升資助效能,探索“項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醫學科學科研項目管理範式。在探索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醫學科學研究的特點和需求,在規劃階段、執行階段、交流合作及風險評估等方麵設計合適的管理流程和工具,提升資助效能。
4.結語
在戰略上,如何有效提升醫學科學領域科學基金資助效能,尤其是麵向我國臨床研究領域亟待解決的重大需求、關鍵臨床問題和“卡脖子”問題,是醫學科學領域科學基金麵臨和亟待解決的時代命題,我們應該強調範式引領,可以借鑒先進的臨床研究資助管理模式。在策略上,建議進一步優化基於“改善健康、推動科學、服務社會”為目標的科學基金資助臨床研究模式,促進醫學基礎研究與臨床研究有效銜接,推動多學科交叉融合。在體製上,著力解決科學基金所支持臨床研究的定義範圍、資助模式、分類評審機製、科學評價體係、成果轉化、交叉融合等關鍵環節,推動科學基金繼續發揮引領效應,更有效地支持臨床研究,改善健康結局。
免責聲明:
① 凡本站注明“稿件來源:beplay2网页登录”的所有文字、圖片和音視頻稿件,版權均屬本網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本網協議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複製發表。已經本站協議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下載使用時必須注明“稿件來源:beplay2网页登录”,違者本站將依法追究責任。
② 本站注明稿件來源為其他媒體的文/圖等稿件均為轉載稿,本站轉載出於非商業性的教育和科研之目的,並不意味著讚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如轉載稿涉及版權等問題,請作者在兩周內速來電或來函聯係。






 beplay2网页登录
beplay2网页登录